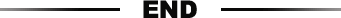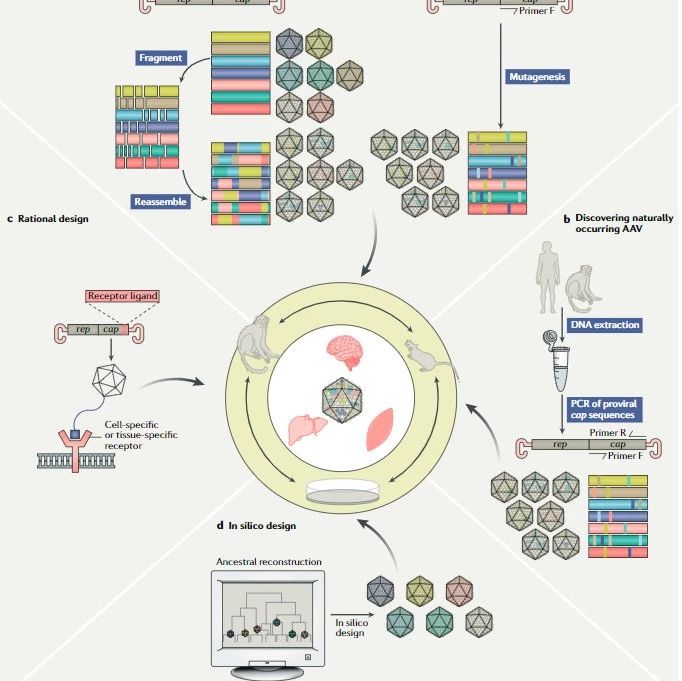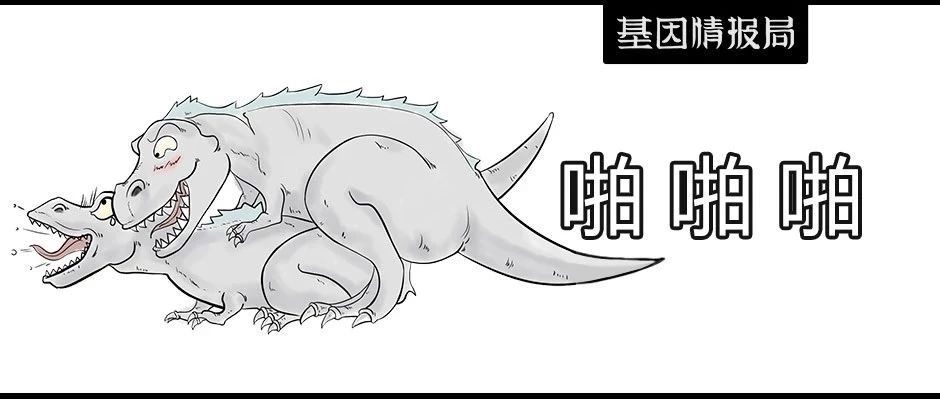如果不懂生物学也能亲手改变自己的DNA,你会做什么?
若能改变自己的DNA信息,你会做什么呢?把患癌几率彻底抹去,还是去酿造能发光的啤酒?事实上,改变DNA信息正是“生物黑客”约希亚·扎伊纳的梦想;而且,无论这一追求让你头昏眼花还是心慌胆寒,他已下定决心:誓把基因工程学推广普及开来。
© Justin Kaneps/ Outside
本文大概
9166
字
读完共需
8.5
分钟
好文章,值得你静下心来耐心阅读
约希亚·扎伊纳(Josiah Zayner)和我正在他位于奥克兰的ODIN实验室里畅饮着荧光绿色的啤酒,桌上乱放着吸液管和实验用的一次性蓝色手套,Red Bull和SlimJim牛肉棒触手可及,音响里跳荡着Drake的歌曲旋律。这不是圣帕特里克节(爱尔兰民族传统节日,以绿色为标志),我们喝的啤酒也没有那么纯粹的绿——那颜色其实来自游荡在大洋深处的水母所发出的冷光,出现在酒瓶中,是因为这啤酒里面充斥着发光水母的蛋白质。
不过,在酿造这种啤酒的过程中,没有水母会因此遭到伤害。扎伊纳是世界上最声名狼藉的“生物黑客”,他喜欢进行超越传统界限之外的DNA和生物系统研究。就拿酿造荧光啤酒来讲,他从基因工程角度,在常规的啤酒酿造工艺流程中增加了网购到的水母绿色荧光蛋白(GFP)基因。如果你知道自己想得到何种DNA序列——比如基因密码里的A、C、G、T等等——其实根本不用得到有这种基因的生命体本身。你只需通过特殊设计、充满着富含无数液态A、C、G、T的DNA打印机来截取相应的基因密码即可,然后就只剩下把新的DNA注入你所希望修饰的有机体内就好了。这个过程,是不是简单得令你目瞪口呆?
我扶着眼镜,想把这荧光啤酒瞧仔细,扎伊纳的独特工艺使酒中充斥着一层薄雾。我不知道这种GFP基因来自何种生物,但直觉告诉我,它绝不是人类常规饮食的一部分。扎伊纳向我保证,这种基因绝对安全。基因工程师热爱GFP,因为从视觉上确认它的存在很容易。他们把GFP与其他待注入的基因相互混合,如果有机体发光,就表明实验成功,而不再需要采集样本进行DNS测序。他说,科学家们已经用GFP基因创造出会发光的猫和老鼠,他们活得都很好。
扎伊纳在奥克兰ODIN实验室的一角
© Justin Kaneps/ Outside
我看着扎伊纳喝下了不少GFP基因啤酒,他的两个耳垂上,挂着十几个尖锐的小物件;经常染色的一绺头发有时蓝色,有时黄色,虽然不能说他看上去很正常,但一定足够健康。
“伙计,”他向我保证,“我们做过且得到了几乎所有的FDA认证,它绝对是无毒的,也不会使人有过敏反应。”为了证明自己的话,他向我展示了自己的左前臂,在“创造美丽”的纹身旁边,有一排四个微小的伤口,“我用自己做的试验,感觉不错。”
扎伊纳声称,他是第一个用另一种生物的DNA对自己进行基因改造的人。在做这件他自己美其名曰科学实验、而在我看来更像是概念艺术的事情时,扎伊纳将自己前臂坏死的皮肤细胞剥离(其实只是在同一个位置用牙刷来回摩擦200次左右),然后用纹身针将水母DNA用力压入皮肤组织。然后,水母DNA会附着在一种可以渗透至人体细胞的普通病毒上,并随之留在人体细胞内。于是,皮肤细胞就开始产生GFP和其他常规蛋白——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无法用裸眼看到发光的皮肤组织,这令扎伊纳很是失望。除此之外,他还自己动手在身上做了一次排泄物移植手术,并成为新进拍摄的纪录片《勇气黑客》中的片段。这次手术,治愈了他的应激性结肠综合征(IBS)。
我并不确定自己会如何看待扎伊纳的种种“怪咖”举动,包括手里发着荧光的啤酒。我觉得,皮尔森啤酒要比水母啤酒更好喝,但我试着保持纯粹的“生物黑客”个性,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我们紧接着灌下了好几杯红色橙汁来掩盖胃肠中可能出现的奇怪感受。但说实话,让这些水母啤酒下肚似乎并不难。就这样,这个从来不吃转基因(GMO)食品的爽快的佛蒙特人,开始对随后的一周有水母啤酒相伴的日子充满了期待。
在我的潜意识里,基因工程无不耗资巨大,相关实验室必须得到财力雄厚的企业赞助,比如孟山都(Monsanto)公司。而将DNA从一个生命体中剥离并注入另一个生命体,也更像是那种需要依赖高技术设备并在数年时间里反复经历实验和纠错的事。但那都是在“Crispr”出现之前的情形了,这种获评2015年《科学》杂志年度突破奖的蛋白,被设计为可以在DNA序列中截取任何你想要的段落,就像是基因的搜索和替换功能。它能在细菌性细胞中起效,因此也适用于老鼠和人体细胞。现在,它已被用于设计产生可以能杀死癌细胞的免疫细胞、能够杀死对抗生素有抗药性细菌的病毒,以及加入罂粟和硕鼠基因密码后,以糖为原料在容器环境下就能生产出鸦片的酵母菌;而被注入这种DNA的雌性蚊子亦无法繁殖(有益于减少蚊害)。但“Crispr”最令人抓狂的一点是,它价格低廉、便于操作使用,这让民间许多拥有基础生物学知识和恶作剧心理的黑客,在自家车库里就可以扮演上帝。
“
这个领域有很多学识渊博的人,也有很多为这门学问疯狂的人,”扎伊纳面带微笑地说,“但很渊博而又很疯狂的却没几个。
”
唯一的问题是,很少有人愿将这些知识与大众分享。这时,扎伊纳出现了。他脱颖而出的方式很传统: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后,成为美国国家宇航局(NASA)科研人员,研究重点是如何让有机体在火星环境下生存。但随后在2015年,他立志成为基因工程学领域如普罗米修斯一般的先驱者,把这门学问从学术实验室带到了普通人中间。
“在这个领域有很多学识渊博的人,也有很多为这门学问疯狂的人,”他面带微笑地说,“但两者兼备的人却没几个。”
我再次向扎伊纳报以微笑,希望看看他有多疯狂。但就现在而言,我更觉得他接近“一只精明的狐狸”。他的ODIN实验室——名称来自英文“公开发现机构”和“启蒙于北方之神”的缩写(Odin,也是北方之神的名字)——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个集综合实验和“快递”业务于一身的机构于2013年成立,旨在令生物知识通过大众自助方式获得普及。ODIN实验室通过网络出售未加工的GFP酵母菌(80美元)、自制“Crispr”主题装备(150美元,汇率1:6.67,后同)、荧光啤酒酿造工艺的主题装备(160美元)和阿米诺DNA游乐场(349美元)。此外,实验室还出售整套基因工程家庭式实验室装备(999美元),包括吸液管、电子管、刻度尺、抗生素、琼脂、轻度激活的细菌、生物性发光细菌、“Crispr”和一台通过聚合酶连锁反应(PCR)复制DNA的PCR仪器。实验室的顾客主要是社区大学和高中就读生,以及神秘的个人消费者。
ODIN实验室所有的装备都是用来设计、加工细菌或酵母菌这些最便宜、最简单生物的,其中重点是GFP这样明显的可视物。这些装备相当于基因工程中的“简易烧烤炉”,能让像我这样的初级使用者快速体验成功的喜悦和其他无数充满诱惑的可能性,而之后如何继续使用则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
© Justin Kaneps/ Outside
扎伊纳和其他“生物黑客”十分看重基因自由。你的身体所产生的所有物质和行为都由基因来编码完成。随着我们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基因基础了解增多——从疾病和寿命到体力和脑力表现——我们也越发有能力对我们的身体进行重新编码。“我认为,我们现在可以对自己做出重大的改变,”扎伊纳说,“而且是比科学家们所允许的更加疯狂的改变。”
很多年以来的大量传言表明,人们对自身所做出的基因改变已然十分疯狂。基因兴奋剂,顾名思义,就是理论上能让任何人拥有西藏山民那样充分利用氧气的功能,拥有勒布朗·詹姆斯那样结实的肌肉,拥有对心脏疾病的免疫能力。所有这些,都能通过基因实现。没错,通过刻苦训练和好习惯的养成也可以获得相应的能力,但如果不借助一定的工具,人们所能取得的进步仍然十分有限。而且,无论是眼下的现实还是并不那么遥远的未来,我们都拥有获得这些工具的途径,这让扎伊纳感到十分兴奋。这是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第一次不必受限于自身通过遗传获得的基因。这肯定会完全颠覆你的观念!”
在基因改造问题上,他从不觉得这应该是企业和研究机构独享的。于是,便有了这台“简易烧烤炉”的诞生——给一个人一块饼干,他可以回味一整天;教一个人如何做饼干,相当于从上帝手中偷来了火种。
约希亚·扎伊纳,这个名字听上去像是星球大战系列中的某个角色。而现实中的扎伊纳也像是生活在科幻剧的场景里:在印第安纳州农场里度过的乡村童年、虔诚于圣灵降临教派并在秘鲁传教的父母(这从名字就可以看出,他的兄弟们名字分别是米卡、扎卡里亚和耶德迪亚,连宠物狗都被取名为耶雷米亚)、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成为黑客组织“地下军团”少年成员的经历、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的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以及在NASA的阿梅斯研究中心所从事的合成生物学研究工作。但在这之后,有些事情开始变得很不对劲了。
对扎伊纳而言,他工作所在的实验室从没发生过爆炸;他也从没因为在与谷歌员工并行时后背冒出水母触角,也没有在山区风景如画的街道上出离愤怒;没有,绝对没有过。真正不对劲的是,扎伊纳发现,在NASA无聊得令人窒息:空荡荡的办公室、徒劳的官僚等级制度,有位上级甚至当面命令他别总待在实验室里。这不是一个立志改变宇宙的人应该待的地方,所以他做出了任何一位初露锋芒的超级英雄所做的事情:成为独行侠。
“
天呐!正常的细菌早已死亡,但改造过基因的细菌则旺盛地长出了新的群落。我们在一天之内就创造出了转基因生物。而这些新生物上万亿的后代都天生带有对链霉菌免疫的基因。
”
2015年,当他在NASA为期两年的工作生活接近尾声时,扎伊纳发起了一项名为Indiegogo的活动,并向参与者提供用于自助进行基因编辑的装备。事实上,早在获得博士学位时,扎伊纳就意识到基因工程学在生活中的渗透程度远超人们的已知,而他早就等不及要把这门此前只属于他所厌恶的精英实验室的学问,带给每一个普通人。原因是,他告诉我,“我一直就是那个穷得掉渣却希望能做出伟大实验的孩子。”活动的宣传视频展示的是扎伊纳在实验室长凳(也是他的厨房案台)旁用长颈烧杯畅饮的场景。这时,画外音问道,“如果你能获得尖端的合成生物学工具,你会用它来创造什么?”最终,这次活动共筹资7万多美元。
活动吓坏了那些批评家。“扎伊纳的活动很让人担忧,因为它与官方的自助生物学领域行为准则的实施相违背,”署名文章曾于2016年获《自然》杂志刊载的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基因工程与社会学中心学者托德·库伊肯(ToddKuiken)批评道。他所推崇的是官方从2008年开始定期组织的非营利性活动,该活动重点在于推动自助生物学研究的安全开展。他举例指出,“从宣传视频的推进镜头就可以看出,他们把盛有样本的培养皿,就放在冰箱里紧挨着食物的地方!”库伊肯同时相信,关于“Crispr”的使用问题,需要开展“激烈的公众对话”。
关于冰箱里物品放置的这番评价让扎伊纳很是气恼。“你的意思是说,做科学实验非得摆出谱来?只有那些能同时用得起两个冰箱的人才有资格做实验?”不过,他的行动也并未落后,也立即买了另外一个冰箱。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当时已被美国联邦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重点审查,一旦查出纰漏,设备获取和网络销售都要受到威胁。扎伊纳也收到了来自德国官员的指控警告——在德国,“生物黑客”行为是被禁止的。不过,扎伊纳的实际业务操作在全美都是合法的,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立法机构还从未宣布该领域为非法,而且ODIN实验室也做得很不错。现在,扎伊纳每年都能卖出上千套基因编辑装备,他本人则希望2017年的毛利能达到40万美元——全世界都需要他的装备。
© Justin Kaneps/ Outside
ODIN实验室的工作时间从接近中午开始,每位雇员都身兼数职,比如在为当天的订单包装物品的同时,新一批微生物的繁衍和培养也不能落下。实验室里,E.coli细菌和年轻男生的体味混合出一种令人沮丧的刺鼻气味,扎伊纳的大哥米卡因此不得不在沙发上把刚刚送到的中餐外卖围上毛巾。扎伊纳将新的金属电线焊接到了之前使用过的PCR机器上(他说,“我几乎没有什么事能做到世界最好,但在eBay上找到最有用的实验室设备肯定是其中之一。”),然后亲自给我演示如何通过“Crispr”将抗生素的电阻注入E.coli细菌之中。尽管一副朋克风的打扮,扎伊纳却很绅士、善良,还是一位好老师。
我们把一些干的E.coli细菌浸入放置在测试管的水中,然后倒入盛有营养液的皮氏培养皿,推到内壁处,再放上一整夜。次日早上,毛茸茸的白色细菌已旺盛生长并占据整个培养皿。我们把细菌从培养中刮出,平分后分别放入含水塑料管中,然后在其中一个管中加入几滴“Crispr”,以使细菌基因密码中单个的A变为C。这一改变将使细菌中蛋白质的电荷在被链霉素攻击时快速地由正变负,从而不再具有抗生素的分子特性。随后,我们把两组细菌分别倒入装有链霉素的琼脂平碟里,在99华氏度(约合37.22摄氏度)环境下进行孵化培育。
24小时后,我将琼脂平碟从孵化环境中取出查看。天呐!正常的细菌早已死翘翘,但进行过基因改造的细菌则又一次旺盛地长出了新的群落——我们在一天之内就创造出了转基因(GMO)生物。而这些新生物上万亿的后代都天生带有对链霉菌免疫的基因。
如果不是这番基因改造,这些细菌肯定会被我们用漂白剂杀死并扔进垃圾桶。这种创造虽然听上去很疯狂,但实际上却相当无害。这种版本的抗生素电阻手段很简单——只不过将DNA序列中的单个字母进行改变——但被改造的细菌却能将改变后的密码传承下去。我们也并非在创造世间不曾有过的东西,但实验室却因此背负了巨大的压力并因此脆弱得像一只年幼的猎鹧犬。而我也不禁想到,这世界上还有很多没有机会去完成实验的“生物黑客”;而且,这门学问如果落在错误的人手中,又会被用来做些什么呢?
我把这个问题踢给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负责部门的埃德·尤(Ed You),这位生化武器应对专家是美国联邦政府的生化武器联络人,他的工作就是要担忧可能出现的生化武器滥用,但他的所思所想显然要远远大过ODIN实验室。“最危险的生化恐怖袭击者,就是我们的大自然母亲,”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人类一直受到越来越多并且反复出现的传染性疾病的侵扰和袭击: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寨卡病毒和西尼罗河热等。如果你想找到某种清晰而真实的威胁,这些就是。所以,我们绝对需要来自生命科学领域的创新成果,从自助式生物实验室开始,来保证我们拥有正确的抵御手段。”
等等,我说。你是真的希望他们自己做些研究和实验?是的,他回答道:“生物学发展极快,但我们又要如何在不阻碍其未来发展的前提下保障安全?如果强令关闭自助式生物实验室,那么你就会遇到一种截然不同的全美安全难题。扼杀创新,只能是我们错过获得新疫苗、新生物防护手段、新应对措施、新行业的机会。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就相当于社会进入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脆弱状态。”
这时候,你会接着指出,生物学领域的快速发展已经使得联邦政府官员难以跟上其前进步伐。但埃德·尤却已经培养出了一种把全国科学家和“生物黑客”视为邻居的思维模式。“他们处在观测前沿技术发展的最佳位置,”他说,“如果约希亚那样的家伙遭到怀疑,他知道自己可以到FBI的旧金山办公室找到他在当地的联络人。”
听到为数不少的政府官员都能有如此进步的阐述,让人感到奇怪,但我咨询过的每位专家都告诉我,他们毫不担心扎伊纳。忘记那些车库捣蛋鬼吧,他们对我说;反而该去担心那些学术研究机构——现在的很多实验室都知道怎样去制造骇人生物。去年,加拿大一位科学家按照电脑数据库备份,人工合成了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灭绝了的天花“近亲”马天花的DNA序列,用这种致命病毒的复活吓坏了全世界。我们是不是正在进入生物学恐怖的新时代?
并非如此,扎伊纳对我说:“我们想象一下,你是世界上最坏的家伙,你想利用生物学伤害其他人。首先,你得掌握这门学问;然后,你还得有设备,并对传播路径有成熟的想法。最后,这还得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伟大计划。否则,你也许只能杀掉一两个人,还不如从厨房拿把刀来得简单。”
“
我咨询过的每位专家都告诉我,他们毫不担心扎伊纳。忘记那些车里的捣蛋鬼吧,他们对我说;反而该去担心那些学术研究机构——现在的很多实验室都知道怎样去制造骇人生物。
”
当晚,扎伊纳和我一起在一家韩式院落餐厅用炸猪耳和日本米酒庆祝了细菌生物改造实验的成功,然后我们又去了扎伊纳时常去授课的一个“生物黑客”聚会地点——逆反文化实验室。在实验室的长凳和无政府主义海报之间,有生长灯(grow lights)照耀下摆满几个架子的奇怪植物和放在大缸里的一颗猪心。一位女士正在尝试通过把奶牛的产奶基因注入酵母来创造素食起司;旁边的一位男士不动声色地排列着他去年夏天从墨西哥采集的蘑菇标本的DNA序列;还有一个小团队在专心致志地设计能够产生人类胰岛素的有机体。为了彰显作为“生物黑客”的大义,他们的创造都将无偿作为全世界的公开资源。
在全球,像这样的“生物黑客”自留地有数十处,比如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基因空间,消息灵通人士可以在这里学习“Crispr”相关课程,并参加“生物黑客”的新兵训练营。如果说美国是“生物黑客”的起源地,那么欧洲已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此外,官方的自助式生物技术网页也已有约5000名注册成员,从麦迪逊到孟买的参与者已留言多达99页。大多数“生物黑客”从不会错过简单的微生物实验,但还是有一些在此基础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大卫·艾希(David Ishee)是一位来自密西西比州的犬类动物繁育者,他正试图将达尔提亚犬DNA中的遗传病基因通过生物技术手段编辑掉;塞巴斯蒂安·科西奥巴(Sebas tian Cocioba)是纽约的一位“植物黑客”,他制造出了一种蓝色玫瑰的基因,所使用的DNA序列分别来自一种能产生高密度蓝色蛋白的热带蚌,以及一种果肉上产生奶牛蛋白的“牛排”番茄。科西奥巴在长岛市一幢公寓楼的12层租住着,但他的所有实验操作都不是在自己的房间完成的。听闻他的高超技术,麻省理工大学(MIT)已邀请他担任一个前沿最高级机密的花卉项目带头人。项目具体内容现在还无法与外界分享,但项目成果很有可能在几年内令全世界侧目。
那么针对人的项目呢?我问道。要等多久,自行车运动员可以开始给自己注射促红细胞生成素(EPO)的基因来促使产生更多红细胞?要等多久,举重运动员才能带着血液中的人类生长因素去比赛?
扎伊纳大笑着说:“伙计,就算没有人正在做这些事,也会有人马上就要去做了。如果说现在所有人都完全无动于衷,我会很惊讶的。这种技术手段现阶段是很难检测到的。那么,你会去做些什么,也去找找DNA?如果一位职业运动员现在找到我说,‘我给你10万美元,帮我做一份我需要的DNA。’我会这么回答,‘靠,那赶紧开工吧!’”
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做法是完全不违反法律的,尽管竞技体育组织一直对此明令禁止。事实上,基因诊疗所若干年前就已经成为运动员和追求延年益寿的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了。给予他们莫大激励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前沿生理学家李·斯维尼(Lee Sweeney)。他向人们展示了一项实验成果:被注射过IGF-1基因(一种类胰岛素生长因素)的老鼠,身体的肌肉组织明显比同类更发达;而被注射过耐力基因的老鼠,在跑步滚轮上一次跑动的距离比同类多出70%,就算这些被进行基因改造的老鼠从不锻炼并且顿顿吃撑,他们也能比同类多跑出44%。
今年6月,一个由美国和以色列科学家组成的联合研究小组宣布,他们发现了一种极为罕见的、能帮助人类延长10年寿命的基因突变。之前在2015年,新兴公司BioViva(字面意是“生物学万岁”)首席执行官(CEO)莉兹·帕里什(Liz Parrish)公开表示,自己将成为首个尝试通过基因治疗以及一定程度上实现返老还童的人。“我是0号病人,” 她在自己的社交媒体Reddit上写道,“明年1月我就45岁了,病痛随年龄与日俱增。”帕里什前往哥伦比亚(基因治疗在美尚不合法)的诊所并在那里接受了有助于延长寿命的基因注射,注射目标除了她的个体细胞,还有块状肌肉生长抑制素,一种管理肌肉萎缩过程的荷尔蒙。
肌肉生长抑制素是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属于那些相信自己能够抵御肌肉的自然衰老并在青少年时期打造出更结实的肌体的人。从人体代谢规律来看,保持肌肉不衰老是件很不易做到的事,因此,肌肉生长抑制素的任务就是:一旦你拥有了足够多的肌肉,它将阻止新肌肉生长;同时被阻止的还有那些不太使用的肌肉的萎缩过程。在网络上,你可以找到很多肌肉发达得像绿巨人一样的狗、牛甚至人的图片,原因正是这些个体身上有这种关闭肌肉生长抑制素基因的罕见突变。
© Justin Kaneps/ Outside
不过,我其实并不那么关心现今运动员的所作所为,我的兴趣点留在我拜访ODIN实验室第一天扎伊纳对我说过的一句话:这是人类历史上,我们第一次不必受限于自身通过遗传获得的基因,我们会因为自己的这次革命而被铭记!
我先讲清楚:不要在家里尝试实施这些基因改造!尽管此时此刻正在实施的基因改造案例可能多达数百个,但很多专家仍然认为,这些几乎能改变人类健康每个方面的技术手段,只有很少一部分被证明是安全的。当你开始搅乱自己的DNA序列,通常会发生很糟糕的事情。比如,你可能会患上癌症,你的免疫系统可能会去攻击他并不熟悉的DNA。后一种情况甚至已有先例:1999年,一位患有罕见代谢紊乱的18岁患者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接受基因改造手术时当场死亡。
另外,患者也不可能为了接受基因改造手术而等上好几年,扎伊纳说。他经常听到人们说自己愿意试试运气。眼下,他正在为一位希望用“Crispr”治疗自己的亨廷顿病(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患者咨询志愿法律服务。同时希望他提供帮助的还有一位正在使用经过基因改造的DNA疫苗来治疗妻子的晚期肺癌的男性。“很多人因为这样的事联系我——‘我很痛苦,你能帮帮我吗?’”
扎伊纳坚持免费提供医疗建议,使患者无需破费就能弄清自己所需要的DNA序列。不过,他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些患者之后会遭遇怎样的困难。“道德约束会让很多人的求医之路步履维艰。当然,我也敢肯定,在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这些国家,很多地方都有实际经营中的基因诊所,甚至已经有能力提供个性化的癌症治疗了——这类诊所未来将会快速崛起。你可以到曼谷街巷里的给一位有基因合成能力的生物学家交上一万美金,然后他在采集血样后的几天之内制造出适用于你的疫苗。”
我脑海中浮现出电影《银翼杀手》中的复制人商店——“我只想复制自己的眼睛”。此时,扎伊纳脸上露出了滑稽的笑容并扬起脑袋,“想不想试试一直萦绕在我脑海的一件恐怖的事?”
现在,来看我们概念艺术的最后一块拼图。我和扎伊纳用棉签擦拭着皮肤上和嘴里的微小裂隙,再把带着黏性物质的棉签伸进装着蒸馏水的管子里打转。然后,我们把所有东西倒入琼脂平碟,进行整晚的孵化培育。
第二天早上,约希亚的那个平碟里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我的却爬满细胞。“看看这些生长旺盛的新酵母,”扎伊纳有些嫉妒地嘀咕道。而我所想的只有——如果这个能成功,肯定会给“家庭酿酒”这个词赋予新的含义。
我们将两人琼脂平碟里的东西刮出来,分别放到微量离心管里,那里提前放置的一些化学液体将有助于使细胞壁松弛下来,以便新DNA的浸入。我们再用吸液管分别向管内滴入10微升的水母DNA,摇匀,静置几个小时。然后,我们把微量离心管里的东西浇到了新的琼脂平碟里,也浇了一些在我们的手指上。“如果这个实验成功,我也许会为此专门推出一整套装备,”扎伊纳默念着。
© Justin Kaneps/ Outside
可惜,这时候我该去赶回程航班了。于是我把自己的那个培养皿封了起来打包带走,同时带走的还有一副黄色染色眼镜盒和一盏蓝色的LED灯,后者能让荧光更容易被观察到。TSA(美国联邦运输安全管理局)可不含糊,绝不会让这些东西被带到机舱内。
随后一天,我收到了扎伊纳的电子邮件:“平碟里长出东西了吗?”
“没错!长出了四五个漂亮的、膨胀着的白色细胞群落。”
“戴上眼镜,然后给它们晒晒LED灯光,看看它们还长不长?”
我照做了,看到十几个即使在LED灯光下也并不起眼的很小的细胞群落,但另外五个更大的圆锥形群落则像绿恶魔一样闪着荧光,“在长,我很肯定!”我回复扎伊纳说,邮件里还附上了一张照片。
“绝了!太酷了!我真是很嫉妒你,我的这份就没成功。”
此时此刻,我的骄傲感堪比维克托·弗兰肯斯坦(Victor Frankenstein)——我用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创造了新的生命。随后几周里,那新生命快速长成山峰状,所发出的绿色荧光已无需佩戴眼镜就能观察到。不管这是何种生命,都是这个星球大家庭的新成员。它们在我家地下室里咿呀学语,等待着与这个世界见面。(译: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