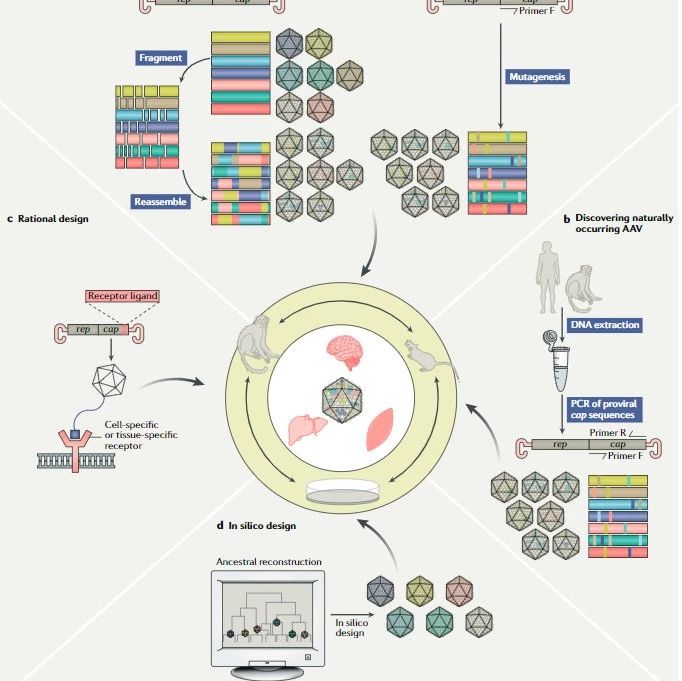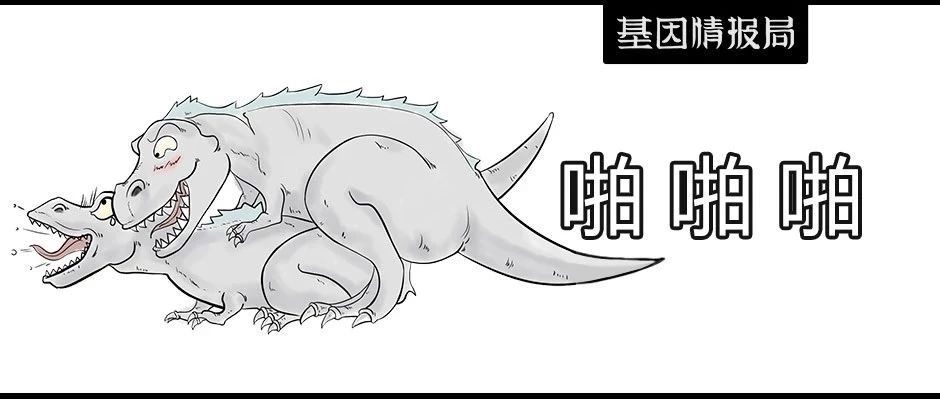基因技术引发的中外典型事件或案例
在因地理和贫困而相对隔离于外界的安徽省大别山区,生活着一个具有同质遗传构造的人群(homogeneous population),人口数达600万。这个地区提供了研究人类基因与疾病的关联性的一个难得机遇,因为从这些“未受污染的基因材料的瑰宝”——相对同质的DNA分子中识别基因变异要容易得多。1996年开始,美国哈佛大学违规在该地区进行了与哮喘病、高血压、肥胖症、糖尿病、骨质疏松等疾病有关的基因样本的采集。数以万计的农民参加了“体检”,先后被抽了一两次甚至多次血样,却根本不知道自己和家人的血样被送到何处以及作何用途。其中,仅运到哈佛大学去的哮喘病基因样本就高达16 400份(大部分来自安徽),还有500个家庭的基因样本被交给资助者美国千年制药公司(MillenniumPharmaceuticals, Inc.)以进行哮喘病等基因的搜寻。这些基因样本将被转化为巨额商业利益,但这些农民却几乎什么也没有得到。[1]此事件在我国并不孤立,几乎同一时期,我国高龄老人的基因也被大肆掠夺。[2]这些事件虽未形成诉讼,但引发不少问题:这些特殊人群及其中的个体,对自身所蕴藏着的特定基因拥有什么权利吗?如果有,在法律上对这种权利如何描述和规范?特别是,作为基因样本提供者或研究参与者,他们能够从对其基因的研究、开发和商业利用中提出财产性诉求吗?此种财产性诉求如何在法律上被认真对待?
2010年,我国广东省地方法院对一起因基因检测(genetic testing)[3]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作出了判决:原告是参加2009年广东省佛山市公务员考试的3名考生,在各自报考职位的笔试和面试总分排名中分别为第1或第2名。但在之后由被告统一安排进行的体检程序中,血液检查(经过一次复查)结果表明原告携带地中海贫血[4]致病基因,被告佛山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以轻型地中海贫血属于血液病为由拒绝录用。原告于2009年12月29日提起诉讼,要求法院认定他们体检合格并按程序进行考察录用,但这一诉讼请求未获两级法院的支持。[5]其实,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和血液病患者完全不同,并无疾病症状,可以正常工作、生活。本案因涉及基因歧视(genetic discrimination)问题,因而被媒体称为“基因歧视第一案”。就报道情况来看,基因检测引发的职场基因歧视并非只有这一起。[6]本案引发的问题是:对求职者进行特殊的基因检测是否应该取得告知后同意(informedconsent)?擅自检测是否侵犯其“身体隐私”或基因隐私?在法律上如何应对基因歧视?基因检测涉及到哪些可能冲突着的基因权利诉求?
2011年,我国“首例血友病产前基因诊断诉讼案”再次被公开报道:原告是血友病[7]基因携带者,于1999年和丈夫一起到被告山西某医院接受血友病产前基因诊断(prenatal geneticdiagnosis, PND),检验报告为“正常胎儿(准确度98%)”。2003年,原告之子在一次意外中左脚受伤,包扎后仍血流不止,经诊断被怀疑患有血友病。2007年,患儿被确诊为“重型遗传性血友病”。2008年3月,原告夫妇以被告产前基因诊断结果有误,导致血友病患儿出生,侵犯生育知情权和优生优育选择权,导致精神、经济上的巨大损害为由提起诉讼,请求赔偿医药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家教费等共计1960万元[8]。案件焦点之一为被告是否具备产前基因诊断的资质。[9]被告以患儿罹患血友病纯系基因突变为由应诉,并拒绝调解。[10]本案引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规范基因医学技术(Genetic Technologyin Medicine)的应用?如何保护个体存在于基因上的可能的权利?如何救济基因医疗损害?
2013年,我国公开报道了一个被称为“救命宝宝”(saviour siblings)[11]的事件:来自江西的一个4岁女孩是重型地中海贫血患者,2013年5月,广州一家医院利用她刚出生弟弟的脐带血(并抽取了一部分身体血液)为她做了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12]为了挽救罹患重症的患儿,父母有意识地选择再生育一个和该患儿血型或组织配对的同胞弟妹,并利用其脐带血或其他基因材料治疗该患儿,这个弟妹就是“救命宝宝”。在这一过程中,往往通过胚胎植入前基因诊断(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 PGD)或绒毛检测技术来确认植入前胚胎或胎儿是否配对成功,或是否携带同样致病基因,只有那些配对成功或没有携带致病基因的胚胎或胎儿才被保留下来。这种复杂的技术应用,在伦理和法律上产生了很多疑虑:为了拯救一个生命而在选择胚胎的过程中“谋杀”那些不符合“定制”要求的胚胎是否具有正当性?“救命宝宝”在其还是前胚胎期时就因“救世主”的角色而具有强烈的工具意义,会否对人的尊严(human dignity)等价值形成冲击?“父母”是否拥有对后代基因的控制权(生命潜能控制权)?在达到能够判断的年龄时,他或她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有权拒绝这一在出生前就被预设了的“目的”吗?在此之前,父母或者其他实体可以有完全的代理权作出脐带血、骨髓或其他组织捐献或其他处置的决定吗?
不仅在我国,基因医学技术引发的法律纠纷或争议在其他国家早就大量出现过,特别是在生命科学史上的最伟大工程——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 HGP)完成之后。仅在2013年上半年欧美就发生了几个争议事件:
一是“海拉细胞”基因组序列公开:2013年3月11日,来自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European Molecular Biology Laboratory)和德国海德堡大学人类遗传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Human Genetics, Heidelber)的研究人员公开发表了世界上最著名的人体细胞系的基因组序列。[13]这个细胞系就是来自一个已死去60多年的黑人女性海瑞塔·拉克斯(Henrietta Lacks)的“不死的”海拉细胞(Hela Cells)[14]。这项研究的负责人拉尔斯·斯坦梅茨(Lars Steinmetz)与其研究小组立刻陷入争议之中。原因一方面是海拉细胞的提取和公开并未获得拉克斯本人的告知后同意,另一方面是这一公开也使得拉克斯后代的基因特征同时曝光,但研究人员也未获得他们的告知后同意。[15]事件让人们继续反思:拉克斯及其后代对这个海拉细胞系(HeLa CellLine)及其未经修饰的“复件”或衍生物,能够拥有什么人格或财产权利吗?
二是“安吉丽娜效应”:好莱坞影星安吉丽娜·朱莉(Angelina Jolie)2013年5月14日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自己经基因检测确定携带着乳腺癌致癌基因BRCA1,为降低患癌风险已进行了双侧乳腺切除术。[16]2015年3月24日,朱莉又在《纽约时报》上宣布自己已于上星期实施双侧卵巢及输卵管摘除手术。这一事件再次触发对基因检测风险、基因上的自己决定和隐私保护等问题的新一轮讨论。安吉丽娜对自己基因信息的公开披露,事实上也泄露了家庭成员的基因隐私,但她并没有透露她在基因上的这一自己决定是否获得了家庭成员的同意。同时,也有文章质疑她背后牵涉着巨大利益关系[17]。虽然一个月后BRCA1和BRCA2两个基因专利已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告无效[18],但人类基因上的财产诉求、基因专利及商业利用、基因检测的可及性等问题依然处于舆论漩涡。
三是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EEOC)2013年5月公布的第一例在《基因信息非歧视法》(GINA)[19]下提起的基因歧视诉讼案处理结果:EEOC指控Fabricut公司在一个女性临时雇员琼斯(Rhonda Jones)申请永久工作的体检程序中,因“认为”她有腕管综合征(carpaltunnel syndrome, CTS)[20]而拒绝继续向她提供职位的行为违反了《美国残疾人法》(ADA)[21],ADA禁止歧视残疾人或被错误地“认为”是残疾人的人;同时,询问她的家庭病史(属于基因信息)的行为违反了GINA禁止基因歧视的规定,GINA明确规定在雇用程序中不得询问求职者的此类信息。[22]本案表明,哪怕法律已经制定,基因歧视行为还可能出现。因而,通过何种适当的法律政策和实施机制来应对这些已发或潜在的社会忧虑,就相当重要了。(系列案件详见《基因权的私法规范》一书前言,限于篇幅注释删除)